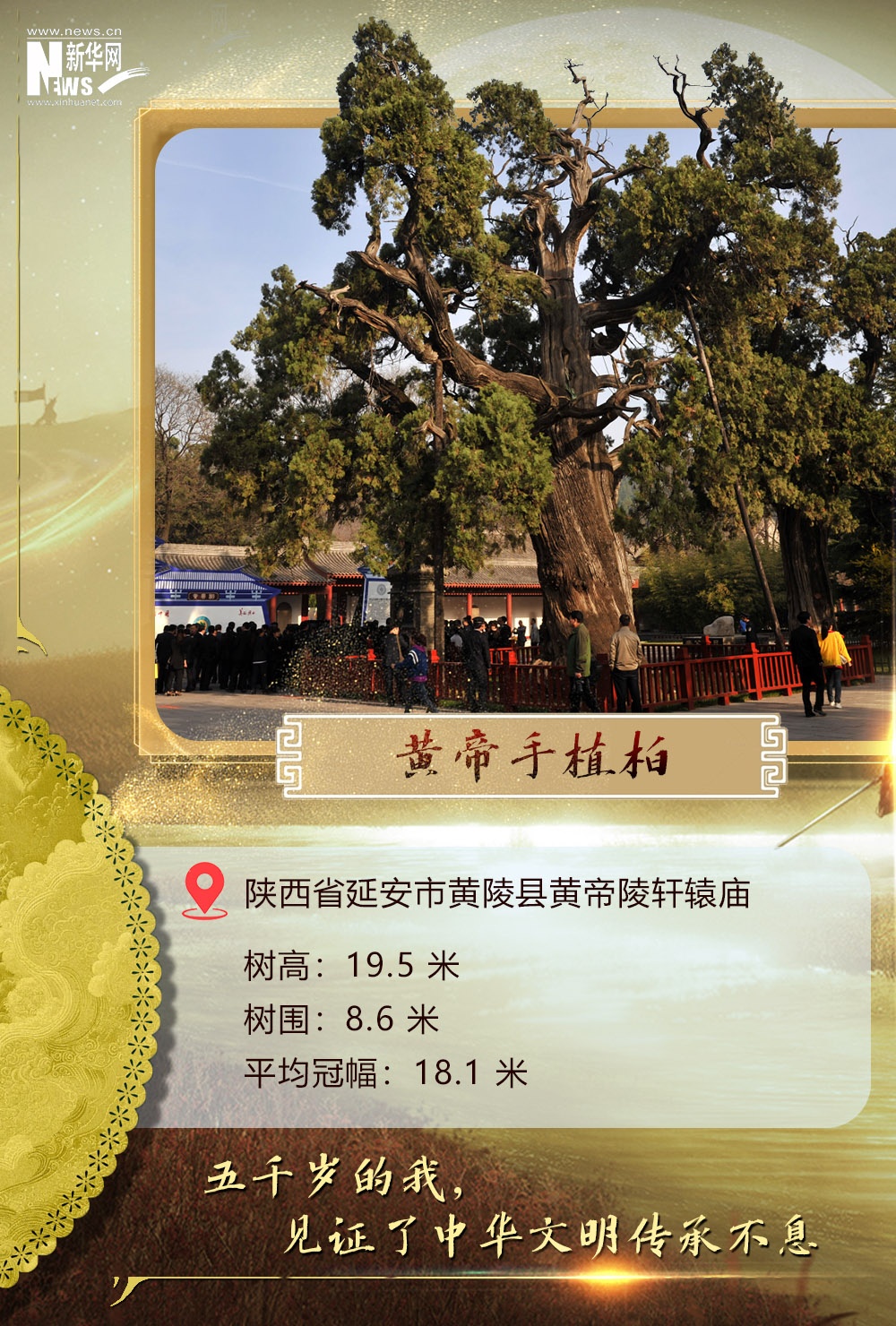小火箭配置链接无法复制
民间资本进入航天领域后,带来了灵活的市场化机制。民营航天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调整产品和服务方向。在卫星互联网、太空旅游等新兴领域,民营航天企业凭借灵活的机制,能够快速布局并抢占市场。

在海南文昌拍摄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大门外的火箭模型(2024年6月29日摄)。当晚,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毗邻的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从2023年开始,世界航天发射活动高度活跃,发射次数、发射质量、航天器数量都不断刷新历史纪录。2023年,全球共完成223次航天发射,合计发射航天器2945个,创造了运载火箭发射次数和航天器年度发射数量的历史新高。到了2024年,这个纪录再次被刷新:全球全年发射运载火箭265次,入轨航天器2795颗。

在去年底的珠海航展上,银河航天创始人徐鸣这样描述:“节奏被商业航天力量打破了。商业航天力量引起的产业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那么对于中国的商业航天来说,为什么真正的黄金机遇期才刚刚到来?在轨道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民用火箭发射需求缘何成为最大的增长点?“发射火箭”这样投入巨大的事业,民营企业又需要以怎样的角度发挥出自己的优势?
以过去两年的发射数据为例,2023年美国共部署2248个航天器;2024年,美国共发射154次,入轨航天器2399颗,其中SpaceX公司发射的“星链”卫星占绝大部分。而中国在2023年共实施67次发射,部署航天器218个;2024年共实施68次发射,入轨航天器257颗。
传统航天强国俄罗斯发展势头大不如前,2023年共实施17次发射,部署航天器数量较少。2024年俄罗斯共实施17次发射,入轨航天器100颗。而欧洲在2023年表现不错,部署277个航天器,其中“一网”星座132颗。但到了2024年,欧洲发射了仅3次,迅速掉队。
从技术积累和体系建设来看,美国在航天领域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其航天项目涵盖了从基础研究到前沿应用的全链条。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商业航天企业如SpaceX、蓝色起源等在可重复使用火箭、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我国的航天近年来发展更是格外迅猛,形成了独立完整的航天技术体系,包括载人航天、卫星通信、深空探测等,在载人航天、北斗导航系统、嫦娥探月工程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并在商业航天领域快速崛起。
从政策支持与战略重视来看,美国政府将航天视为维护其全球霸权的战略高地,持续投入大量资源用于航天技术研发和军事应用。
我国政府将航天事业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出台政策支持航天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2024年商业航天作为“新增长引擎”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年)》的实施,为社会资本进入航天领域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引。地方政府也积极响应,北京、上海、广东等十余个省份密集出台专项支持政策,形成了多个商业航天产业集群。
反观俄罗斯,虽然在航天领域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但近年来受到经济和政策调整的影响,航天发展速度有所放缓。而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本就落后,进入商业航天时代,发展滞后,航天项目更多依赖国际合作。
对于中国来说,传统航天领域优势积累已经足够深厚,商业航天爆发式发展的外部和内部条件已经完备。
我国的航天领域开放发展,并不是从这两年才开始的。早在十年前,我国就首次向民营资本开放航天领域——“北京二号”成为首个经政府批准的民用商业卫星项目。到2018年5月,中国首枚民营自研商用亚轨道火箭“重庆两江之星”成功发射;同年,“双曲线一号”火箭首飞成功,证明了中国在商业火箭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

今年2月17日,民营企业座谈会召开,引发各界热烈关注,商业航天领域也有相关企业参会。可以说,商业航天从政策层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机遇期将至。
以SpaceX为例,2023年SpaceX进行了98次火箭发射任务,占全球发射总数的44%。这些发射任务总计达到1082吨,共部署了1984颗星链卫星,并将1600吨有效载荷送入预定轨道,占全球的80%。
它建立了垂直整合的制造体系小火箭配置链接无法复制,自主研发和生产火箭发动机等关键部件,避免了传统航天企业依赖外部供应商的高成本模式。例如,通过自主研发Merlin发动机,采用汽车工业的铸造工艺,允许一定瑕疵率。它的猎鹰9号火箭采用模块化设计,80%的零部件可通用,减少了重复设计和生产的成本。这种设计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降低了研发费用。同时,它还广泛使用3D打印技术制造复杂零部件,如发动机燃烧室,并采用不锈钢材料替代碳纤维,不仅降低了成本,还提高了火箭的耐高温性能。
此外,SpaceX借鉴互联网行业的“快速试错”方法,突破了传统航天领域的“零容错”文化。通过频繁的测试和迭代,和高频率的发射任务,形成了规模效应,进一步降低了每次发射的边际成本。例如,2023年SpaceX完成了98次发射,占全球发射次数的44.34%,其载荷占比更是高达80%。其“拼车发射”服务,是针对中小型卫星提供的一种低成本的发射方案。
又如,我国的商业航天独角兽银河航天,在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成的新一代卫星智能制造工厂,形成年产100-150颗卫星的低成本批产能力,其单颗卫星研制成本已从传统卫星的亿元量级降至千万元量级,未来有望进一步降至百万元量级。其推动卫星从“少量定制”向“批量生产”转变,未来有望“像生产电脑一样生产卫星”。
从航天活动的商业化和市场化角度来说,与传统航天项目相比,民营航天企业在卫星制造、火箭发射等领域展现出更高的研发效率和更低的成本。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模式使得航天活动更加经济可行。
中航证券航空航天首席分析师王宏涛认为,“商业航天并非一个单独的板块,更多的‘商业航天+’才是核心。”据王宏涛团队研判,2025年商业航天核心市场规模超过3000亿元,加上关联市场整体的年度市场规模可能接近万亿元。
民间资本进入航天领域后,带来了灵活的市场化机制。民营航天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调整产品和服务方向。在卫星互联网、太空旅游等新兴领域,民营航天企业凭借灵活的机制,能够快速布局并抢占市场。
太空作为战略高地,具有重要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价值。轨道资源在国际上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属于稀缺资源。当前,各国国家队发射能力和密度都难以满足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民用火箭发射需求激增,商业航天成为占领轨道资源的最佳选择。
在火箭回收与重复使用技术方面,蓝箭航天的朱雀二号火箭计划在未来两年进入商业运营阶段,朱雀三号可重复使用火箭已完成10公里级垂直起降返回飞行试验。在基础设施方面,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于2024年11月底建成并成功首发,标志着中国商业航天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
2025年,中国商业航天的产业生态正在逐步完善,形成了从火箭制造、卫星组网到应用服务的完整链条,涵盖上游的火箭和卫星制造、中游的发射与运营、下游的应用场景拓展。
上游主要涉及火箭制造、卫星制造及相关配套设备。近年来,中国在航空航天复合材料领域取得显著进展,市场规模从2020年的500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764.59亿元,预计2025年将达到874.23亿元。卫星制造行业总收入也从2020年的80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132亿元,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中游环节包括卫星发射、地面设备制造和卫星运营。2023年,中国全年共实施67次航天发射任务,其中商业发射占39%,达到26次。2024年商业发射次数进一步提升至33次。同时,卫星运营市场规模也在稳步增长,2024年收入达到804亿元,预计2025年将突破982亿元。
下游市场主要面向传统和新兴应用场景。传统领域包括通信、导航、遥感,而新兴领域则涵盖卫星互联网、太空旅行、太空采矿等。2024年,卫星互联网市场规模达到404亿元,预计2025年将增至447亿元。
航天芯片需要具备抗辐射、耐极端温度等特殊性能,技术门槛极高。目前,我国部分关键芯片IP仍依赖国外厂商,例如高端宇航级FPGA和CPU芯片。传统宇航级芯片如SPARC架构芯片虽然稳定,但功耗较高且不适合智能化处理。同时,航天芯片的生产成本高昂,部分宇航级芯片价格极高,例如赛灵思(现AMD)的宇航级FPGA单颗芯片价格可达数十万美元。国内现有宇航级芯片大多采用传统加固方法,导致芯片面积冗余增加,成本和功耗上升。
为避免芯片技术瓶颈制约我国商业航天在大规模组网、高通量通信和全球运营能力的提升,新兴技术开始涌现,例如RISC-V架构逐渐受到关注,其开源性和灵活性为国产航天芯片提供了新的机遇。一些国内企业正在攻关双核锁步RISC-V内核等技术,实现底层核心IP的全自主研发。3D封装技术的应用也为航天芯片的小型化和高性能化提供了支持。
2025年,国际合作将成为中国商业航天发展的重要方向。随着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的运营、多款可复用商业航天火箭计划发射、手机直连卫星商业化应用发展,我国商业航天有望在海外市场取得突破。
展望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将进入从“补短板”到“锻长板”的转型升级期。政策支持将从基础能力建设转向引导创新突破,投资结构将向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
通过技术创新、产业链协同和国际合作,我国商业航天有望在卫星互联网、天基测控等细分领域实现“换道超车”。